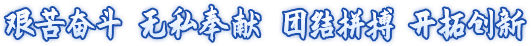2021年08月23日 新浪科技综合
8月10日,河北邯郸永年区居民李先生去医院做核酸检测,突然听到有护士喊他,说是“正在给一个小伙子打疫苗,小伙子害怕,特别不配合,让过去帮忙按住。”李先生力气挺大,按住了。

时间再早一些,微博有热搜称:@铜陵平安郊区 老洲派出所辅警慈曾龙执勤时,突然一年轻男子向他求助。该男子从小恐针。最终,男子全程用力抱住慈曾龙的腰部,完成疫苗接种。

看到这些,我的心情很复杂。
作为一名资深的“针头恐惧”者,在本次新冠疫苗接种中,我也给同行者留下不少“要保存一辈子”的精彩瞬间。
比如,因为叫得太惨,旁边那组接种都停下手,光看我了。

图片说明:那个面目狰狞的就是我(本文作者提供)
以及,别人都是一对一接种,只有我,享受双人服务:一个人打针,一个人扶住我(防止我跳起来逃)。

在观察区,同行者都来关心、安慰我,“放轻松,不要去想”。
“但那不管用。光想到针头要刺破皮肤,那一刻就像世界末日了。”前两天,我看到BBC发文,讲述一位23岁“针头恐惧”者的接种经历。这句独白说到心坎里。

小伙名叫亚当,数次尝试接种疫苗,都没成功。
第一次,他花了数周,才鼓足勇气、预约接种。人都走到接种中心了,没敢走进去。
第二次好点。他进屋花了5个小时,从极度恐慌,“克服”到能坐在看清针头的地方。但还是没接种。
3天后,亚当又来了。他和护士们在一间独立房间,待了3小时。试过缓慢呼吸、分散注意。“就差那么一点。最后一刻,我还是怂了。”

怕打针,怕到晕过去
“‘针头恐惧’是特定恐惧的一种,在医学分类上属于恐惧症范畴。”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陈俊主任医师如是说。
就像有人怕蜘蛛、有人怕老虎那样,“针头恐惧”具有恐惧症的共同特征,即明知自己的反应(怕针怕到行为失常)是非理性的,但就是无法控制,出现过度的恐惧和焦虑感。
陈俊主任说,程度较重的“针头恐惧”,可能表现为“想到就瑟瑟发抖”“都不敢想”。更严重些,可能发展出“强迫”行为、迫使自己避开“危险”。简单说,就是:坚决不打针。
美国佛罗里达州心理学家亚瑟·布莱格曼告诉CNN,自己有一个咨询者,受“针头恐惧”困扰多年。“我最近问她,会否接种新冠疫苗。她表示真的非常想接种,家里所有人都已经完成两剂接种。但她对打针的恐惧,已经远远超越对死亡的恐惧。”
英国焦虑症协会的“针头恐惧知识手册”指出,若真按住这些“针头恐惧”者、迫使其接受注射,他们可能出现急性焦虑反应和惊恐发作,表现为心跳加速、呼吸加快、出汗、血压下降,甚至晕厥。
“因为过度害怕,他们可能突然变得好斗。有时,三四个成年人都压不住一名‘针头恐惧’者。”“针头恐惧知识手册”写道。

图片说明:日前,马来西亚一名男护士因为“针头恐惧”,在4名健硕同事的“陪伴”下,终于完成一剂接种。/星洲日报
“那么大的人了,还怕打针?”
“‘针头恐惧’很常见。”陈俊主任安慰。
2018年的一项荟萃分析显示,大多数儿童都存在“针头恐惧”。在青少年中,其发生率约为20%-50%。到二三十岁,发生率降为20%-30%。该分析还称,16%的成年人、18%的长期护理机构工作人员、8%的一线医护及27%的医院其他工作人员,会因“针头恐惧”而逃避接种流感疫苗。
回到如今的新冠疫苗接种,英国国家健康研究所和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医学研究中心调查显示,在1.5万余名受访成年人中,有1/4者“怕打针”,且年轻人群发生率相对较高。同时,美国心理学会和该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报告称,5000万美国人因为害怕打针而不接种疫苗。
“‘针头恐惧’往往来源于既往的不良经历。”陈俊主任解释,小时候被父母摁着打针、特别疼,以后每次看到针,就会唤醒那段“恐怖”记忆。但下一次,针不能不打,于是又被摁着。一次又一次地,我们的创伤记忆被强化。

前文所说的亚当告诉BBC,恐惧源于8岁那年打耳洞:痛,感染,更痛,久久不愈。
也有一些人,是通过“其他途径”,获得这种记忆。“就像怕鬼并不是因为见过鬼,而是看过鬼片。”陈俊主任说。
有一项56名“针头恐惧”者的研究显示,24%者的“心魔”是“看到其他孩子打针时的痛苦表现”。
悲催的是,由于现代医学有大量的血液检测和注射行为等,“针头恐惧”的发生率在升高。有数据显示,1980年代,有20%的儿童害怕打针;而到本世纪初,这一比例升至60%。
《疫苗》杂志2017年发文称,罪魁祸首不是“接种疫苗的数量”,而是“频率”。“如果孩子一天要接种5剂疫苗,5年后,有50%的可能性会发展成‘针头恐惧’。若按一天1剂、分5天接种完,恐惧会明显减少。”
除去“后天习得”,一部分“针头恐惧”是“先天遗传”。“这是人类进化千百万年的成果。那些小心谨慎、避免尖锐物品刺穿身体的人,活下来了。而大大咧咧、不管不顾的基因,断根了。”陈俊主任认为,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“针头恐惧”相关基因。
怎么才能不害怕?
“许多父母宁可拖着孩子,任他们大喊大叫、乱踢逃跑,做一些很尴尬的事,苦熬着打完针。但这不是唯一的选择。”UC Heath家庭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凡妮莎·罗林斯称,“针头恐惧”可以治疗。诱因不同,治疗方法也会有差异。
凡妮莎·罗林斯认为,若不干预,一部分“针头恐惧”可能会进展到害怕医疗检查,拒绝手术和必要的医疗植入物。若是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(1型糖尿病)患者恐针,那会有生命威胁。“针头恐惧”还会影响到教育、旅行、怀孕等。
陈俊主任建议用认知行为疗法,进行“系统性脱敏”。“先和恐针者聊聊,打针是什么感觉。等他不紧张了,看些静止的图片,再过渡到看注射相关的视频。接着,让他进入接种现场,看实物,慢慢地让他接受注射。”
若一个人压力太大,以至于无法接受行为治疗,那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,抗焦虑和镇静催眠药物能够让身体和大脑放松下来。
此外,保持有节奏的呼吸、转移注意力,也有一定效果。“要做深长、有节奏地呼吸,不要屏气。”凡妮莎·罗林斯写道,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对孩子很管用,包括听故事、看视频、玩玩具等。
“网上有个视频,讲一个医生给孩子打针,特别温暖。”陈俊主任记得,那个医生先用针管,挠孩子脚底。

他一边唱着歌、捏孩子大腿,让他放松,一边用针管到处戳,宛如游戏。

在孩子笑呵呵的时候,医生拔掉保护套,完成注射。
都打完了,吹泡泡庆祝一下。

“如果新冠疫苗接种常态化,针对‘针头恐惧’者,我们需要有一些更人性化的接种方案。”陈俊主任表示。
目前,英国设立多个“特殊人群疫苗接种点”,鼓励“针头恐惧”者和朋友、家人一起来。这些接种点有独立房间。“针头恐惧”者在预约时,可以提前了解“防针恐方案”。到接种日,接种护士会在其完全准备好之后,再下针。在整个过程中,人们随时可以喊停。
截至本文发布,亚当已再度预约接种。他感到“乐观”,认为自己这一次能成。